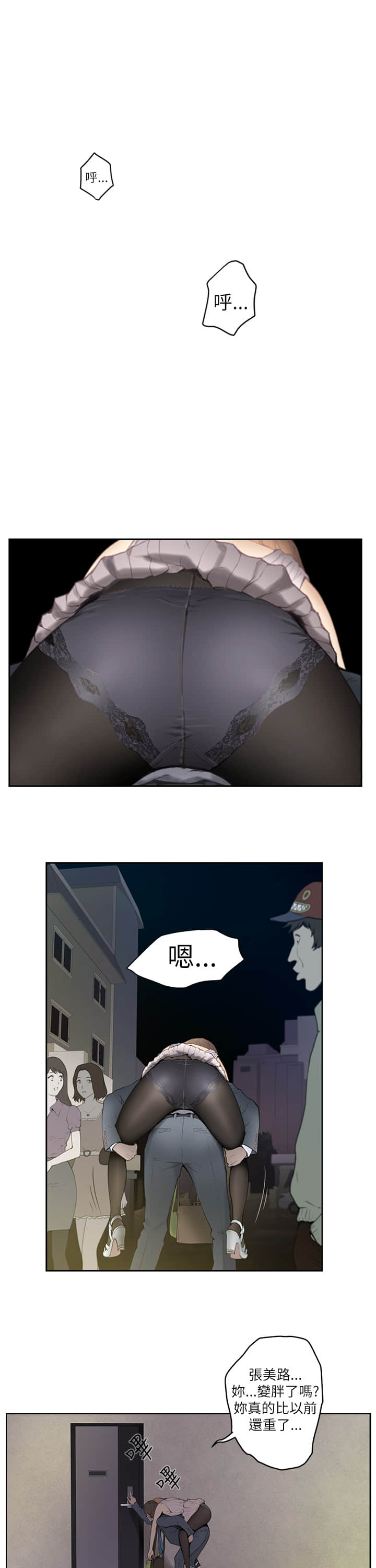摘要:
一 我上大学的时候是父亲送的我。父亲对我怀着鲁迅塑造阿Q的复杂心情,对我的大学则抱着阿Q见到王胡的简单态度。在车上,他嘀咕着:“没听说有这么个学校,反正别当回事,就当...
摘要:
一 我上大学的时候是父亲送的我。父亲对我怀着鲁迅塑造阿Q的复杂心情,对我的大学则抱着阿Q见到王胡的简单态度。在车上,他嘀咕着:“没听说有这么个学校,反正别当回事,就当... 一
我上大学的时候是父亲送的我。父亲对我怀着鲁迅塑造阿Q的复杂心情,对我的大学则抱着阿Q见到王胡的简单态度。在车上,他嘀咕着:“没听说有这么个学校,反正别当回事,就当一架破梯子”。父亲说这话的当儿,我仿佛看见一小乞丐在淮师里摇摇欲坠。我讪讪地笑起来,并不感到怎么绝望,心里自嘲,“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父亲见我居然能笑出来,确实恬不知耻,斜睨着我,补充一句:“还不如一所好高中”!
我们把东西放在风雨球场的门口,旁边是英语系的新生接待点。几个女生坐在接待桌前跟一个男生说笑着,荡气回肠的样子。后来我一直很羡慕这份打情骂俏的肥差,但我的表演欲从没得到满足。等我办完手续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交了一个朋友。我一看,竟然是高中时的同学松,还有他的父亲。范父不如家父健谈,总是点头笑着。我看到父亲有这样的倾诉对象,感到很欣慰。新松毕业后支藏了,为了这跟他老父大吵一顿,却是这时想不到的事。那会儿,风雨球场门口的泥沙还裸露在外。父亲说着说着,不幸被卷起的沙尘迷了眼睛。父亲愤慨地说,学校开到农村来了?几个英语系学生愕然地看着父亲。
父亲当天下午回合肥的。不记得他临走有没有跟我说什么。晚上打电话回家的时候,他还没有到家。
到了宿舍,看到陌生的同室,心里怯怯的有种疲倦感。挑了一张对门的下铺,倒在床上,想着明天要干些什么。几个室友在聊天。有人说,天啊,我怎么来的,我填的不是这破学校啊。有人和着,我也是我也是。
我听着心里很自卑,因为我是自愿的。我感激这架破梯子,它救了我的一生。事实上,我和数学师傅势同水火的历史很悠久了。笨伙计费了吃奶的力也弄不好他们的聪明活。师傅嘴角下沉,瞟他的时候眼睛就像轻佻的晨风掠过水面。有一年徒弟弄好了另一副活,一篇小文章。他的语文师傅很欢喜,用毛笔字抄下来贴在黑板旁。小徒弟高兴得魂不守舍,整天做着美丽的梦。数学师傅是班主任。一次上课时,他挥舞的粉笔“不小心”划破了小徒弟的梦。破碎的宣纸丑陋的挂在墙上,哗哗哗,迎风招展。所有的小徒弟盯着这个小徒弟。师傅轻嗤了一声,继续忙活。小徒弟的眼睛和脸都火辣辣的。
有个室友很活跃地跟人打招呼,他见到一个人就说,你好你好,我叫超,安庆人。我看了他一眼,那小子真帅。天涯何处无芳草,到处都有安庆人。我们寝室就派了两。
来的第三天军训。那个当兵的半个月来只教我们走路。我本来会走路的,被他教后变得不知道怎么走路了。有一次,我被他在臀部捏了一把。他还很不满地说,怎么回事?叫你提臀咋不提臀?软乎乎的!
休息的时候总有同学的才艺表演。我嘴巴里叼着一根草,看着他们。不记得他们唱的什么了,也不喜欢在我受难的那些天里,有人用歌声来粉饰太平。只记得我旁边是个女孩,她看我竟然吃草,轻轻地笑着。那时有谁会在意我呢?那个当兵的最后很受伤。大会演时评N个优秀教官,团长数来数去,都是N+1个,最后才揪出他就是那1个,他不请自来的。说良心话,他很认真,把我们弄得很惨。
二
军训那几天,秋老虎发威。脸皮晒得泛起油花,明晃晃地勾引着太阳。我那一双逼仄的小眼,泛滥成了水帘洞,遥看瀑布挂前川。里面的猴子早已热晕。
历经八十一难,猴妖也能成圣佛。白天一顿烘烤,晚上还想榨一块“豆腐干”,一篇美化苦难的广播稿。那些白天软耷耷野鸭,一到晚上统统亢奋起来,嘶吼的内容无非是,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豆腐坊”设在厕所隔壁的水房,虽怪味飘荡,幽幽缕缕,似无实有,却也只有彼处的灯光通宵不灭。经常“拷问”自己:若不是为了浮名,我会忍住满身困意,通宵达旦的泡公厕么?回答是否定的。我的好友汉重,四年来致力于情书这一块的辛勤开发,可谓术业有专攻,真情比草原广阔。情为何物,他有体会。即便是他,我也没见过在厕所里写情书。这所在有时夜市繁华,拨吉他的,斗地主的,考前突击的,还有扯嗓子嘶上一口的,那就堪称裂帛了。
一连好几天,我留意学校的广播,都没有听到我深夜激情的轰炸。于是,我的驴性犯了。我要说出真实的想法,我憎恶自己站在操场上那六神无主的丑样,抬头,挺胸,收腹,还提着臀。什么人必须得受那样的漠视和惩罚?我的无聊无比深广。
有天晚上,几个室友躺在床上闲扯,那时都还不熟,不知怎么就扯到写文章上了。不知怎么我就卖了个狂,说写文章我要做淮师第一。不知怎么刘汉重就跟我抬杠,笑着说这不是高中,你想第一就第一啊?我斜睨着他,甩了一句,我到哪儿我的笔就一定要做第一。这家伙轻佻的笑杀伤力极强,撩得我浑身颤抖。后来才知道汉重的情书也是淮师一绝。这家伙身怀异秉,每见一窈窕女子,口中止不住地莺莺燕燕,不知其所呼,回到宿舍必再唱孟庭苇的那首“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
我在大学里发过许多毒誓,欲羞辱对手导致其疯狂的,欲使对手嫉妒导致其吐血的,欲让对手后悔致使其自残的,只有这一次是不致命的。发完誓,我就回到厕所。后来每念及这个誓言,只好暂收玩劣之心,躲在学校图书馆的六楼一隅,将脑浆涂在一页页方格纸上。
想起来那四年中毒誓不断,几乎件件都是如练“七伤拳”,不是每个毒誓都能毒倒对手的,真的是先伤己再伤人。那些痛恨自伤的夜晚,那些涂满悲壮的小路,在记忆中都渐走渐远了,但发誓成瘾,只怕以后还是少不得吧。
后来有一天,在食堂门口忽然听到空中布满熟悉的字符,那是我的一篇新闻稿。我一路呼啸地跑上五楼,想站在高处纵声一呼,那播音却已经停止。 【】
三
自从那次在风雨球场门口看了一群男女荡气回肠的公演,我就知道权力真是个好东西,哪怕是贱一回的权力。现在想起来,他们在打情骂俏的百忙中,还抽空瞥了我好几眼。其实,他们的眼睛空荡得一如我外婆的口腔,但在当时,我的热血不小心沸腾了一下,赶紧低下头把衣服的下摆撩直,将蒙着煤灰的皮鞋藏到范氏父子的身后,逮了个机会,冷冰冰地回射他们几眸子。自己琢磨着演得还挺到位。
力必多和权力这对奸夫淫妇,从来是秤砣离不开秤杆。必须承认,我垂涎权力这可爱的淫妇已经很悠久了。我既充满表演欲,却不具有表演的权力,理所当然地感到了太史公的痛苦;我想,在小波那里,我这欲贱不能的惨状就叫给阉割了!经我明察暗访,才知道大学里想沦为奸夫的最佳渠道是进学生会。所以,我有了生命里的第一次竞选。
在进入会场的那一晚,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紧张和无助。我像个痨病鬼似的呼吸紧张,脚步发软。周围全扎着奸夫们陌生的脸孔,那上面明灭着一双双像是饿死鬼似的眼神,清一色地,都像要逸出氤氲绿气来。我搜索每一片笑声的来源,疑心他们是否早已得到内幕。我悻悻地想,这群畜生什么都干的出来。于是,我下意识地瞄了眼前排坐着的几个老师,一个个岸然得像巴黎圣母院里的克洛德。我开始怀疑我那文绉绉的竞选台词是否足够煽情了,其实它已经被我写成了一封情书,那上面叙写着我对一个风骚淫妇的刻骨相思。那时节,我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惧。作为无神论者的我,颤抖地念了声,主啊,救救我……
什么都来不及了,竞选开始了!有人上去,有人下来,跑龙套似的。我紧张地目睹他们将野心包藏的严严实实。他们的笑容是那么柔软稀松,水一样地漫在脸上。有个家伙显得很激动,他双手箕张,捧在胸前,做出一副将心掏出的虔诚姿势。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我想,这奸夫,太绝了。
前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那听起来多么陌生的两个字。我的心刹那间忽然轻盈起来,不错,那个叫“毕清寒”的人与我又有什么关系?他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境。我作践的只是我自己。
不知道怎么就上得台来,仿佛立于山巅,底下是雾一般飘渺。我似乎开口了,底下居然一片掌声,哗哗地,仿佛许多小孩被他们的母亲抽打着屁股。我似乎说了什么可笑的话,底下一阵哗然,如同臭粪坑里升起嗡嗡的苍蝇声。我的嘴似乎从我的脸上独立出去,做了力必多的俘虏,它鼓荡的唇舌好像山寺夜里纷飞的黑色蝙蝠,充满嗜血的激情。
我后来知道,从那天开始,我的人格就是分裂的了。我和一个叫毕清寒的人习惯了相互出卖灵魂,我有怎样卑鄙的事都由他来替他完成。但同时,我也知道,至少我还是真诚的。
当晚宣布了结果,我不在其列。第二天正式的通报上出现“毕清寒”的名字。一个月后,他因为拒绝在“三八”节那天为裙钗们操一篇通讯,而被永远地踢出了那个组织。
四
我竞选系干之前,已经在院报记者团干满一个月了。这个组织里有十来号人,八个是干部,余下几个不幸沦为干事。我是办公室主任,原则上该分管团里内务。我一有机会就把校报整垛整垛地偷回宿舍。练习书法,或者给几个弟兄如厕。后来他们陆续有了女友,就不再用我的报纸了,说怕得痔疮。于是,我就把整盒的订书钉往回拿,我现在订书用的还是当“主任”那会儿的钉。
不到一年,两个干事前仆后继地卷了铺盖。临走时,其中一个数学系的嚎叫着:“一个个日妈的鸟样,指手画脚,八个差遣老子们两个,出去你们算个屁”!
干事们走后,我们还真苦了一阵子。社里分派任务下来,团长交代给团副,团副交代给五个部。五个部长眦牙裂齿,心有灵犀地看着我:“见者有份”!我心里骂着,去你们妈的,向校报推荐稿子的时候,怎么不拉上老子!
我在团里的唯一盟友李伦佑经常对我说,某某真不是东西,背后出阴招。他说的某某有时是团长有时是哪个部长。李伦佑和我都喜欢暗箭伤人,我们凑在一起只谈人非不说人是。我们经常为如何巩固在团里的地位而忧心不已。
没过多久,社里决定招聘干事,过程分初试和复试。初试那天,我和李伦佑监考一个教室。那是个飘着细雨的下午,湿气里透着微冷。我现在依然记得,当时心事重重的脚步怎样失魂落魄的游荡。很偶然地,我在一个女生旁边停下,看着她写这个雨天下午自己淅淅沥沥的心情。她的文字很好,写的很有感觉。我不禁自失起来。
她忽然回过头来,吃惊而孩子气地看着我。说实话,她相貌平常。我笑了笑,真心地说:“写的很美”!
“真的?”她抿嘴笑了,眼睛很有神采,“谢谢你”!
我敷衍了一句,找李伦佑去了。
我在团里干“主任”那会儿,还在班上编“杂志”,一份油印的小册子。我的小册子本来不叫“秋水”,叫“丑小鸭”。
五
丑小鸭是我的写作老师卢银波想出的。当时,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他旁边请他给杂志取个好名字。老头也挺支持,他略微想了想后告诉我,小册子呢才开始办,名字可以叫的朴素点,丑小鸭,蒲公英什么的就挺好。我的大牙不小心爆了出来,怕他再说出“映山红”之类,赶忙说,是,是,总有一天我们会变成白天鹅的!老头看我懂了他的良苦用心,很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可我最终没用“丑小鸭”这号。毕竟四年太短,只争朝夕,进化的过程太慢太无聊。
“秋水”只淌了一季就旱得焦巴干。那时同学们都知道纯文学穷途末路了。我愁得几晚没睡,想出个办法,就是把杂志上的好文章推荐给校报。校报有稿费。
我拿着《秋水》去校报的时候,柏编辑正带着几个小记者阅稿。我在人堆里忽然看到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她一直看着我笑。我知道她被录用了。
有一天阅稿到很晚,我知道她住的宿舍离校区较远,我开玩笑地问她要不要送。她看了我一眼说,你说呢?
当时,我的女友不知在图书馆的哪层楼里一边等我一边诅咒我。但,我不能拒绝那个眼神。
我们走在路灯下,踩着前面人的影子,漫不经心。她一路低着头,我跟在后面东张西望,一边想她为什么不会撞到电线杆上。到了她住的地方,我准备走。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说:“陪我坐一会,好吗”?
于是我们在一个木椅上坐下来。星星一如虫声般地在夜空里唧唧喳喳,月亮像一只孤飞的大鸟,拼命逃脱喧嚣。不记得那时我们说什么了,却记得我说话时她似笑非笑的眼睛。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干了一件想起就掌嘴的蠢事,不知为什么,我用手抚了一下她的头发。她孩子似的依顺地看着我,却不吃惊。
一切虫声都寂寞……
我无法向她解释,这种举动是出于她的头发很好看,我也不能说因为我从小就有好动症。那个晚上,我咀嚼着浓厚的罪恶感夜不成眠,虽然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没过几天,我和她又在校门口碰到。她跟她的朋友们在一起。她很开心。当她准备向她的朋友介绍我时,我像个瞎子似的熟视无睹,一头扎进人堆里。
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喂,喂,喂了好久,有个温和的声音哽咽着说:“我们有仇吗”?
我手一抖,不知怎么就挂断了电话。
六
现在,当我企图梳理上大学那会儿的鸡零狗碎时,有一件事,仿佛肚脐似的将那四年划为两截,上半身丰腴下半身撕裂。那就是我办了一本叫《守望者》的杂志。
在此之前,我可是个有精神生活的人。虽然腿脚不长但走路带风,经常,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喋喋不休。其实我心里没太多想什么,有时一首老掉眉毛的歌就够我打发几里路的。我周而复始地哼着,不厌其烦。我喜欢徒步。我走路的时候脑子转得飞快,思接千载。我的许多喷香的主意都是走出来的,脚下一停,脑子跟着就钝了,跟闹钟松了发条似的。刻薄鬼也许会说,所谓“有精神生活”,正是像精神病人一般的生活。我不反对。我若反对,便是坐实了你的馊理论——精神病人如同醉酒者,醉了偏说:“我没醉,嘿嘿!喝——喝——”。
办《守望者》前,除了唱歌,有时路上还想着另外两样东西:时间和女人。
据我想,这两样东西本质何其相似!既感性得要命又理性的让人痛恨。你无法永久地占有她们的青春,美丽甚至真诚。当然,她们也休想。她们首先不能拥有大多数男人的忠诚。我们还是顺差!
某天上午,当一个叫关中鹏的人说找我合办文学社时,我很是意外。这件事我在走路的时候没有想过,在发誓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写东西的人结社好比两对男女当街比赛接吻,都跟所做事情本身不相干。此前,我一看到文学社仨字,鼻尖就浮想联翩,于“豆腐小贩”们扁担箩筐的交错中,嗅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馊黄豆味儿。
但是现在,这个透着中年气象的家伙告诉我,清寒,咱俩一块办吧。我的脑子和嘴巴瘫痪了数秒。我听到的仿佛不是这些,而是:“兄弟,入伙咱干一票吧”。数秒之后——我爽快答应了他。这个选择让我从此觉得自己深不可测。日后每每侧目深思,汗颜于自己的朝秦暮楚。如今一想而通,我跟其他同类又有多大分别?都是些毫无诗意而野心勃勃的家伙。
七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我说办文学社,却不能就有文学社。在没有上帝的地方,领导的意图你要深刻领会;在没有大领导的所在,小领导的意图你更要深刻体会。可怜见地,小领导压力大脾气跟着就大。他们往往都有一股率真的品格,即当着你的面发泄对你的厌恶,丝毫不加掩饰,把你当自己人似的。听者无不如沫春风。有段佳话:某系学生会 小汪据说当场梨花带雨痛改了前非,彻底地当了一回自己人。
我原以为这次要当自己人了,心里既忐忑又激动。岂料,院里那个小领导没把我二人当自己人,他显得很见外。小领导说:“别多事!不是有文学社了么?我们堆着欢:“不怕再多一个,为同学们服务。”领导不屑:“不就是你们自己想当领导么!”我们垂着手:“由您领导!”小领导说:“上面有指示,严禁大学生私下拉帮结社。”我们正色地说:“哪能。正在跟您汇报着嘛。”领导愤怒了:“我得到消息,你们暗渡陈仓,已经搞起来了!”我们抵赖:“谁说的?不可能吧。”小领导忍无可忍:“趁早给我歇!否则你们系跟着受处分。”
出了门,我们相对黯然。蔫蔫地用各自的方言痛骂姓单的小领导。我骂道,去他*的。关中鹏骂道,日他奶奶!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的合作还算默契。
底下已经聚集了一批同志,我们不能就这样停了。唯一的法子,求助于本系。我们添油加醋,极尽挑拨、扭曲之能事,把小领导的威胁冰雹似的砸向系党支部书记。末了,委屈地说:“书记,您看着办吧。”书记把嘴巴咂吧得啪啪直响,说:“小单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赶紧跟了一句:“他不把学生当人。”书记嘿嘿笑着,大手一挥:“你们想怎么办?”我们立刻狗儿嗅到骨头似的,说:“听您的!”
那书记实在值得一书:虽是不惑之后,两眼依旧眨着无穷疑问,有不知就里者以为这是童心未泯,着实可亲。上前接洽,方知受了表象的愚弄。每次见他自办公楼出来,两肩左挑右晃,蹑手蹑脚,不禁想起《西游记》里的巡山喽罗:“不好了,大王,洞外有个毛脸和尚叫着要师傅呢!”
不管怎么说,书记帮助了我们,把文学社留在中文系里。现在,我依然感激着他。不管怎么说,我的精神生活行将结束,我再也不能袖着那台破随声听在校园里作夜游神了。别了,我的 spiritual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