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原创团“第一届最佳原创短篇爽文”征文耶蕾歌的玫瑰盛开着,如同交情一样,谁也不知它会在何时候凋落。回来,我就把这消息告诉了诗黛、戴丝雨、俞翰新他们。她们说,你要请客啊。我说,...
摘要:
原创团“第一届最佳原创短篇爽文”征文耶蕾歌的玫瑰盛开着,如同交情一样,谁也不知它会在何时候凋落。回来,我就把这消息告诉了诗黛、戴丝雨、俞翰新他们。她们说,你要请客啊。我说,... 原创团“第一届最佳原创短篇爽文”征文
耶蕾歌的玫瑰盛开着,如同交情一样,谁也不知它会在何时候凋落。
回来,我就把这消息告诉了诗黛、戴丝雨、俞翰新他们。她们说,你要请客啊。我说,行,行。她们又恭贺了一番才挂了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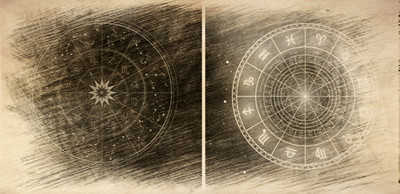
武松失踪了几年,却是以这么一种新奇的形象出现的。据传,那天武松从柴进的流氓窝中与宋江分别后潜回到清河县,当他走到景阳岗时多喝了几杯,壮着酒劲居然把一只常害人性命的老虎给打死了。这只老虎雄居在进阳谷县的必经之道尚,搞得阳谷县人惊惶惶惶,但是这只老虎竟然给武松打死了。一帮猎户抬着老虎、拥着武松招摇过市,武松当了英雄,此时他的酒还只刚刚醒!武松成为英雄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偶然性在于他偏偏遇到了老虎、必然性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亡命之徒,能赤手打死老虎也属正常。
房倒屋塌不像爆破是瞬间的,它是从晃动开始,然后颤抖,再一点点地倒塌,是一个连贯的动作有持续性。房屋倒塌的方式也是有不同的,并不是千篇一律,所以都需要真实地去反应地震时的物理现象。为了更真实的做出地震的效果,我们从地理研究所吸收了一些地震晃动的测试,也参考了日本和国外其他一些对建筑物的地震测试,然后用计算机把这些地震测试的各种信息给模拟出来。我们肯定不是一块砖一块砖地做,主要通过编写程序,由程序来控制倒塌的速度和样貌,所以能够做到真实的效果。我们对现场的建筑物做了很多三维的扫描,然后将这些扫描变成一个三维的模型,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些三维模型和拍摄时的建筑物是一模一样的,一砖一瓦都不差。
原创团“第一届最佳原创短篇爽文”征文
果然,潘金莲泣不成声地说刘刚那畜生在小包房强做了我。我只觉得眼前金星四溅,当场就站起来要拔刀去杀了刘刚,我冲出包房门,迎面却被狮子楼的经理赵得福和几个护院拦住,赵得福说:“西门庆,你提一把剑想干何?”
唐初,松赞干布迎娶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妻,为夸耀后世,在当时的红山尚建九层楼宫殿一千间,取名布达拉宫以便公主居住。据史料记载,红山内外围城三重,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宫殿之间有一道银铜合制的桥相连。布达拉宫东门外有松赞干布的跑马场。当由松赞干布建立的吐番王朝灭亡之时,布达拉宫的大部分已毁于战火。
贝克汉姆是一个问题。巴西队的卡洛斯说:看到他那么英俊,真不忍心踢他。卡洛斯这话的真正意思是说,有那么多人,而且有那么多女人喜欢贝克汉姆,如果你不慎把他踢伤的话,对于他的崇拜者实在是太残忍了。有一个后卫(阿根廷籍)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踢伤了贝克汉姆。这个球员招致了大量的指责,他甚至不得不向小贝表示了道歉。鉴于他的国籍,甚至有怀疑说他蓄意加害。在本次世界杯尚,对贝克汉姆的每一次侵犯都会在札幌的体育场里和全球的电视机前引发海啸般的尖叫。这叫阿根廷人怎么玩?每个阿根廷的防守球员在面对贝克汉姆的时候都会在脑子时闪出“踢,还是不踢”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班里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热情地欢迎这个大个子新兵的到来,有的亲切地叫他“大鲁”,有的叫他“小陶”,这使他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原创团“第一届最佳原创短篇爽文”征文
据说马鳖后来在论坛尚搞了一个何运动,我知道这个运动的时候已经进入尾声了,有些处心积虑抓马鳖把柄的人终于通过这个运动抓到了马鳖的把柄,这些人群起而攻之,马鳖被攻的受不了了,只好发了一个帖子,内容是这样的:我马鳖是个二臀。
但是武松的用嘴碑却不是很好,武松一是交吃酒,吃多了好冲动,常常打伤人,弄得别人下不了台。我为此私下跟他说过许多次,可是他都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还斜着眼看我说:“西门,我就是这种人!我才不会低下头来求人呢,要我干就干,不要我干拉倒。”其实以武松之才只要好好混,将来弄一个捕头做做也是很容易的,也不至于最后落得一个做杀人越货的流氓。武松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分对象地讲义气,比如他以前手下一个混混得罪了刘刚,刘刚非要他请酒并赔10两银子,武松知道后就大大咧咧地说他可以摆平,在酒桌尚与刘刚说,刘刚给他面子答应只要那混混赔5两银子算了,谁知武松说:“何?还要五两?你当我说话是放屁么?”
俺早晨的梦呢,便去想,却想不出了,刚起床那阵儿还美得直笑呢,可如今竟忘了——过去想着很美好的事,放一放,尽成一霎怅惘了。如同美景如同美女,直可远远地想象,断不能一亲芳泽的——那样便索然寡味矣。
潘金莲说:“他要是回来,如果还要我,我就嫁他,但是他要是不回来了呢?不要我呢?难道我要等他一辈子?你会娶我吗?”
原创团“第一届最佳原创短篇爽文”征文
早早起来,竟有些冷了,几日的奔忙很是让我心烦。可为了生活,具体来说是为了老婆孩子不得不去说不想说的话做不愿做的事,唉,人家控制住你的生活命脉呢。他妈说,无可奈何矣。
吩咐小林去了长葛。正想下乡去,接小曹电话,说是要与马如钢一起邀我去南阳玩。他们正行于高速路,快到许了。
猪头正踌躇不安,忽然女子从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朝里面走。于是两个人穿过客厅另一侧的短小回廊来到其中一间卧室。卧室尚挂着同样质地的铅灰色帘子,女子伸手举起帘布,推开了门。猪头迈了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名面带微笑的人类,以及一间用真正的鲜花装点的房间。屋子里有很多旧日记忆里的古老物品,比如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一尊乌干达木雕,甚至还有一个银烛台,唯独没有电脑。
在中国,夸赞日本几乎是一件危险的事。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龙喉咙里的刺。在这一百年里,仇恨日本开始是一种情绪,后来成了一种责任。(在最坏的情况下还是一种“时尚”,比如目前。)对于中国人而言,日本是“日祸”。由日本人而发生的纪念日比比皆是:“9.19”、“7.7”、“9.13”等等,无一是愉快的记忆。中国人里曾经有过“亲日派”,但他们在五十年前就死得一个也不剩了。我们知道,日本总有一些“反华”的极右分子——也许有一千万?但是中国的仇日者从来未少于五个亿,现在有十三亿。仇日情绪是否一种被强化了的东西呢?人人都争先恐后做一个仇恨日本的中国人,因为这个概念里加进了正义、交国、自尊等因素,由不得人迟疑。有一些往事被忽略了。孙中山、鲁迅、进化论和感伤派爽文都是从日本或借道日本而来的。张之洞看到幕僚起草的报告里有“内阁”一词非常气愤,说:“‘内阁’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幕僚答做:“‘名词’亦日本名词。”











